
▲ 启发

公元1881年 清光绪七年
9月25日(八月初三),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家大院里,出生了一个男婴。其父名作周伯宜,家里的长子,是一名秀才,此时居家赋闲。母亲名作鲁瑞,是此地举人鲁西曾的三女儿,虽没念过书,思想却颇为开通。
这男婴的祖父名为周福清,字震生,是清同治十年(公元1871年)辛未科进士,此时正在北京城任职。当抱孙子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,恰巧张之洞来访,于是他便以所遇情形为其孙取乳名为“阿张”,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大名为:周樟寿,字“豫山”。这豫山便是日后的鲁迅。
公元1888年 清光绪十四年
小豫山已经在周家大院里生活了七年,周家的百草园便是他玩耍的主要“阵地”。单说这百草园可不是一般用来装饰大院的小园子,它的主要用途是种地。园内南宽北狭,总的下来有2000多平米,可以称上是一块周家的自留地。农收的的时候就腾出一片空地作晒场,等到过了秋收也就闲置了,转年春天可不就是“百草”园。园子总体是偏于长条状的,西北角突出一块,有个外门通向河沿,方便农耕用的粪土和木灰的接入,南方多以水道作运输,也算很常见。
此时,七岁的小豫山也迎来了自己的开学礼,进了私塾。当时小孩入学多以名字的字为日常的称呼,又因为绍兴口音缘故,就导致“豫山”这两个字被同学们取笑为“雨伞”。小豫山便请祖父改名为“豫亭”,接着不久又改为“豫才”。此时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出生,初名松寿。
公元1892年 清光绪十八年
已经十一岁的周樟寿离开了他的百草园,进入三味书屋开始跟着寿镜吾先生读书。相当于开始上初中,但这“初中”却上的异常曲折,以至于前前后后上了六年之久。这里面的原原因,我们到后面再细讲。说回三味书屋,这寿镜吾此时四十有三,是同治年间的秀才,由于痛恨洋人且看不惯当时清廷丧权辱国的作为,便放弃仕途,在家设立学堂收徒。但是这位先生的学堂教学风格与传统相差很多,所以并不是很景气,据说是一年收的人超不过8个。当然,这里所谓的传统便是教授奔着仕途去的四书五经,而寿镜吾先生教的所谓的“不正经”,却也仅是荆轲刺秦一类的侠义故事,放现在来看,反而是一个很德才兼顾的教师。
关于寿镜吾的模样,鲁迅曾在《从百草堂到三味书屋》里面提到一位先生的描写:“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,须发都花白了,还戴着大眼镜。我对他很恭敬,因为我早听到,他是本城中极方正,质朴,博学的人。”至于他是不是寿镜吾,就无从考证了。其实,就算是寿镜吾也不过分,毕竟早先时候六十就古来稀了,再者说他这倔脾气上来一夜白头也不是完全不可能。
公元1893年 清光绪十九年
50多岁的周福清接到母亲病故的电报,由于当时官员的父母之丧称为“丁忧”,须离职守孝三年,于是他依制回到故乡。但此时还乡的周老爷子,心里可谓五味杂陈。回望自己混迹官场二十余载,好不容易被实授了个内阁中书的位置,刚刚坐了五年就奔着告老还乡去了。这内阁中书在清朝官阶是从七品,相当于内阁临时挂职的职员,负责平时的撰写、翻译等工作,挂职一段时间后有了机会再调去地方做大官,而其中关键就是等机会,所以他这一走,三年后怕是难再复职了。再看看身后的儿孙,儿子周伯宜如今也三十有二,还仅仅是个秀才,几次乡试又都不如意。在这多重的因素之下,周福清孑然一身,老周家家室的转折也就此出现。
9月,转眼到了该年的乡试之期。此时,周福清得知今年赴浙江主持乡试的正考官是殷如章,是和自己同年的进士,一同在翰林院工作过,也算是旧识了。这个消息使得周福清再次打起了心中的小算盘,便带上银票和他的仆人陶阿顺赶往苏州码头去提前迎接殷如章。
要单说这件事,在当时的清朝一定不会绝无仅有,但偏偏这时的周老爷子偷了个懒,关键时刻掉了链子,让仆人陶阿顺自己带着钱票和书信去了殷如章的船上。咱也不知是这老爷子一时糊涂还是硬好面子,但这船上的人可不止主考官殷如章一个人,还有那副考官周锡恩、苏州知府等好几位大人。陶阿顺把书信往殷如章手里一递,殷如章是瞬间反应过来了,没敢拆封就把信放边上了。可偏偏这陶阿顺自个非要“抖个机灵”,喊了句:“大老爷,这信您可收好咯,里面还有上万两银票呢!”这么一来,殷如章是彻底没了法子,把信推给了身前这几位,“这事您几个看着办吧”。
周福清到这里算是彻底栽了,心想也就只能跑路了。可他这一跑,儿子周伯宜就跟着遭了殃。先是被关进大牢,再剥去了秀才身份,周老爷子见此情景只得去自首。然而周伯宜这人虽被放了出来,经了这一遭的心却受不住了,心灰意冷,忧郁成疾,便落下了肺病。要说这古代的读书人的身子也真可被称作“弱不禁风”,常年待在屋里看书,不好锻炼身体,又见不着阳光,但凡心里再添个堵,人也就基本去了一半。再说回这老周家,顶梁柱一下塌了俩,自此也便家道低落,过起了卖地买药、当物救囚的日子。此时的鲁迅还叫周樟寿,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,自此随一家人去了乡下。
乡试收买考官,这无论在当时和现在都算得上是大罪了,但是周老爷子这定罪却又是一处悲喜交加的遭遇。重罪上报朝廷,按以往就是直接死罪一条,可这年却赶上了慈禧老佛爷的六十大寿,死罪是不兴在今年的,所以给判了个从轻发落。但是犯了大罪也就没那么轻巧,后面还有光绪帝这一道判,娘俩向来是死对头,又给周老爷子改成了斩监候,意思就是暂时不斩,秋后再斩。只是这秋后也是大寿之年,所以就干脆推到了第二年。周家人一看,有机会了,就又卖房又卖田的,四处活动,待到第二年期满前又给推长了一年。
公元1896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
周老爷子入狱的第三年,也是死刑被后推的第三年。这或许听起来些许荒唐,但也确是事实,毕竟这周家的家底也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比的。然而,长子周伯宜的肺痨病是越来越严重,慢慢也就成了现在讲的:肺结核。要论当时的医疗能力,能治好肺结核的高科技还要等个五六十年才能出现。因此,即便有治病的钱也是没治病的药,最终周伯宜因肺结核不治身亡。这对本就走下坡路的老周家更是雪上加霜,此时十五岁的周樟寿(鲁迅)开始有了写日记的习惯。
公元1898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
4月,17岁的周樟寿离开家乡来到南京,投奔名叫“椒生”的叔祖,即其祖父周福清的弟弟。自此,入了江南水师学堂(洋务学堂)。期间却发生了一件转折意义的事情,叔祖“椒生”虽在洋务学堂做官,却非常不喜洋务,是个“守旧派”。因此,他以周樟寿进入洋务学堂为耻,认为其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,遂将“樟寿”改为“树人”。自此之后,“周树人”这个名字便得以出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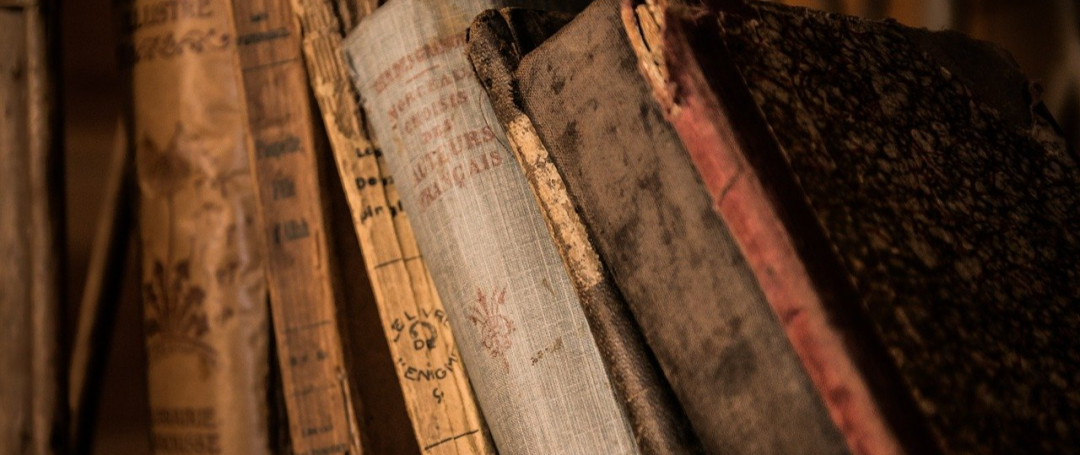
▲ 感悟
章尾
以上便是鲁迅家族大起大落的童年往事,由此也可以看出,其童年是趋向于没落和曲折的。个人认为,也正是因此造就了鲁迅日后的写作风格。作为家里的长子,早早扛起大梁,实属不易。至于之后的鲁迅是怎么样求学,又是怎样弃医从文的,我们在下一章【周树人的斗争】中再展开细说。